你踏着一地深深浅浅的黄土,匆匆走来。甩起杨的手,推弯柳的头,用你的玉骨冰肌展示威严。你银装素裹,粼粼寒光,映得青山失去颜色,映得湖水不再蔚蓝。
你是一首淡而隽永的诗,色彩时而是一种总体的白:从原野到天空,从晨雾到月色。除了白,就是黑:黑的树杆,黑的淡淡的万物的轮廓,黑与白有着一种抽象的力量,是从繁杂生活中提炼出的精粹,是世间最为简洁明快的色彩。

你纯洁得坦坦荡荡,可眼神为何那么忧伤?头发不再青长?看天空变得灰暗,大地失去娇颜。可谁又说过这是你的错?看那寒风中挺立的苍松,看这冰雪中傲放的腊梅,何处又不是你力量的凝聚。谁说这山谷变得苍凉,它正在无遮无拦中集聚,在静默中吟唱,看着万物生灵,都睡得正香。
冬天虽然没有春的碧绿,夏的火热,秋的凉爽,但冬天自有冬天的壮美。一场大雪,铺天盖地,一夜之间,大地变得银装素裹,分外洁白。不仅如此,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”;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……冬天的雪,还是古今诗人吟颂赞美的对象,缔造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章。
不要短浅地萎缩视线,关闭心扉。放飞呆滞的目光,在冬天的腹地驰骋,你的思想将会收获冬天的原色和韵味。在坑洼的堤堰上,村民们掀起了水利冬修的热潮,他们精心地修补家园,面带微笑地迎接款款而来的新年;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全社会向下岗失业人员伸出了温暖的援手,再就业工程和送温暖活动,使成千上万的家庭走进了冬天里的春天;人们围坐在炉火旁,家事国事天下事地猛侃神聊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被冬天的真挚情谊拉得很近很近。
热爱冬天,并非爱其赤裸裸的自然景观,而是一种在其他季节无法寻找的感觉——人生内涵。冬天,只垂青于那些勇敢和勤劳的人们,懒惰和丑恶会在冬天里瑟瑟发抖;因此,只有经得起严冬的考验,顶得住雪压和霜打,才能领略鲜花吐艳的美妙,春风秋雨的真谛。
冬天,让我们锤炼了不屈的傲骨,茁壮了生命的刚毅,纯洁了高尚的灵魂。冬天,让我们拥有了透彻的醒悟,蓄积了无尽的砥砺,从而赋予我们新的希望。让我们用有力的臂膀,热烈地拥抱冬天。(《天津老年时报》王建华文)
杜鹃花开每回进山,在凉风垭山口,见到那一片杜鹃林,我都会想起一个人——北大生物系毕业生曾周。他的身边也有一棵杜鹃,尽管细弱,却是一棵真正的秦岭杜鹃。
杜鹃树忠诚地陪伴着他,淡粉的花在风中轻轻摇曳,与漫山遍野开得热烈灿烂的同类相比,它未免太孤寂,太冷清,但它仍顽强地伸展着花瓣,努力使自己袒露在春晖之中。这棵细小的杜鹃是曾周的同学从高山上挖来种在这里的,他们走了,不忍心把他一个人丢下,便让杜鹃伴他度过这山中漫长的岁月。18年过去,昔日的同学们成了国家栋梁,成了大熊猫保护专家,走出了国门,走向了世界,我们可以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面孔,而他,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,留在了佛坪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的西侧。
1985年,我来到这里时,他刚刚躺下,他的同学们尚未走远,他们给杜鹃浇的水还没干透。
记得那个夏天,我整天跟着向导刘老汉翻大山,钻林子,林子里很热,也很闷,昏昏然中猛地听到一声绝唱,啼响空山直入白云深处:“不如归去——”
心儿一颤,抬头观望。刘老汉望着白云顶端说是四声杜鹃。又说能叫全四个音的只有佛坪有,尤以三星桥这儿最多。我听过杜鹃啼血的故事,一声啼叫一口鲜血,化作一簇灿灿的杜鹃花,那惨烈的情景让人对那小小的生灵生出无限的爱怜和崇敬。我向四周睃寻啼血的杜鹃,却满目一片绿,寻不见一丝异色。失望中,又听谷底传出一声紧似一声的“不如归去——”但我终于没见到那只精灵般的鸟儿。
那个娃儿,永远归不去了。刘老汉慢腾腾地说。
我问哪个娃儿。
刘老汉说,打北京来的学生娃儿,跟踪大熊猫,从对面那崖上掉下来了……他初进山来也是我给他带的路,后来熟识了,他就自己走……

我就抬头看对面那崖,崖很高,刀削般的齐整,顶上长满了油松,白云擦过,奏响低低的吟唱。
就这样,在曾周的殉难之地,在“不如归去”的啼叫声中我初识了他,由于他的存在,这山这水,这古老的三星桥便蒙上了一层凄绝的悲壮。
在山里,不少人跟我谈起过曾周,说那是个活泼爱唱的大学生,自信中还有那么一点儿固执。三官庙保护站的站长说,那天早晨,曾周背着馒头出去寻找熊猫,天黑了也没回来。大家都急了,连夜打着灯出去找,他的同伴带着哭音儿的呼喊传遍了山的角角落落,加急电话一直挂到了北京林业部……直到第三天,人们才在三星桥的崖下看见了他,他伏卧着,像在酣睡,腕上摔坏的手表停在4月17日晚上8点40分,那是他遇难的时刻。他使用过的地形图挂在树枝上,太陡了,无法取到,只好永远地挂在那里了,像一面飘扬的旗……
我说,三星桥古碑旁应该再立个新碑,让人们都知道,这里不仅仅是有名的古道,更有它辉煌的一笔——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青年将生命奉献给了大山,奉献给了自然保护事业。后来,在三官庙的阳坡上,我见到了属于他的碑——一块未经雕琢的大青石。石上刻着他简短的一生。这精巧又别开生面的墓碑是他的同学们,那伙跟他一样活跃的年轻人的主意。
也巧,那天在山里,我遇见了从广东专程来给他扫墓的他的父母。他们长久地坐在墓旁,默默无语……
今年,我又来到曾周已不算簇新的墓前,天气还冷,墓背阴处的残雪还没有化尽。他的墓碑被重新修过,保护站的年轻人在上面刻下了21世纪守护者的心声:看见你,我们更热爱这片山林。
我默默地与曾周墓相对而立,心内有些酸涩,更多的是自豪。他走得太早,太早……凝望里,他说,在我的身上,他看到了生的可贵;我说,由他的墓碑我知道了死的价值。摘下几朵洁白细巧的野草莓花递给他,在靠近坟墓的刹那,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。
月亮升起来了,远山近树变得清朗透明。融融月光下,我想他或许会由那缥缈的山间走来,因为他就是在那里消逝的……月夜中,我又嗅到杜鹃花的阵阵细香,随着微微的风,空中传来几声“不如归去——”的啼叫,缓慢清脆,四个声儿叫得极全。我料定了,他已与这清风,这明月,这山石,这林海融为一体,无法分开了。
注: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,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,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,情况属实,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,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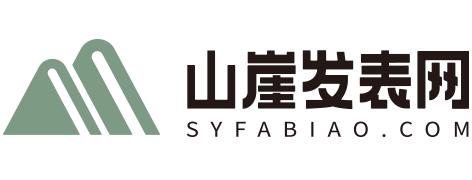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